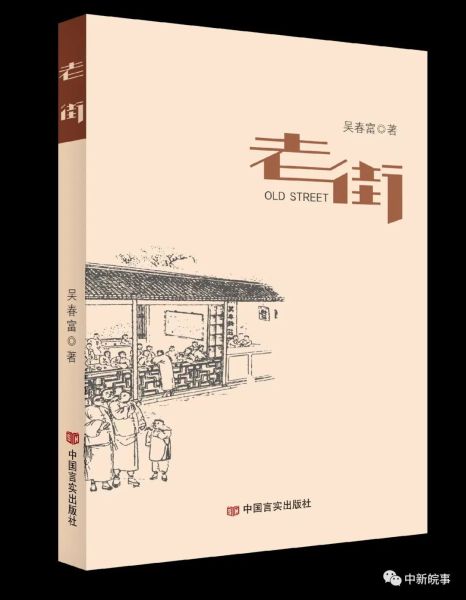
一切写作本质上都是诗意的。
一切生活本质上也是诗意的。这话好像出自海德格尔的笔端。两句话既对应又相连,它承上启下般各自安装了直达装置,因为一切写作本质上都是抒写生活,几乎没有不抒写生活的写作及其写作者,哪怕是很糟糕的作者及其作品,哪怕是闭门造车。当然这里所说写作皆指文学文本,与科学文本无涉。生活是多样的,写作当然也就随之多样化起来,只不过成分不同,多寡不均,搭配不一,显隐不等。
但什么是诗意?哲学家、评论家及诗人们均给出过许许多多见仁见智的文本答案。海德格尔还告诉我们:人是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这一文本提示既是一种折射,也是一种照射,它照射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边边拐拐,不集中地集中着,不统一地统一着。生活千姿百态,文本照射出来的诗意当然也就千姿百态。
根据海氏的这一观点,诗意对于写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写作追求,尽管一些文体比如小说可以不必刻意去诗意,但诗意本质上是一种写作力量与源流,它就蛰伏在那里,也就说这个写作力量与源流直接滥觞于生活本身。一种写作文本生命得以延续的重要气息因此有了获得的可能性。有了这个重要气息的存在,读者便能感知到:这部作品有生命,且生命仍继续存在着。这与我开宗明义提出来的“一切写作本质上都是诗意的”这句话是递进关系。
什么是本质?百度有许多阐释,但就写作而言,我认为本质是一切写作者的写作“前文本”。据德比亚齐在《文本发生学》中的解释:“前文本”是对笔记、草稿、提纲等资料的“解码”。我不怎么认同这个观点。我认为,“前文本”是写作者内心世界闪闪发光的沉淀物,有了这个闪闪发光的沉淀物作为引力作为导向,写作者便自觉不自觉,甚至是不得不,向着这个“本质”出发,并深入这个“本质”内部。

吴春富的长篇小说《老街》也是向着这个“本质”的。向着这个“本质”展开老街的骨架、血肉及老街这个生命个体──老街虽是一条街以及沿着这条街延伸、拓展出来的五店六铺、七巷八弄、九曲回肠,但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存在──因生命需要而流出的每一滴汗水、每一声欢笑、每一星血泪。正如作家洪放在该书序言中提到的一个词:热气腾腾!
热气腾腾本质上也是诗意的。吴春富一直生活、工作在这条老街上,被这条老街耳濡目染、朝夕润化着,吴春富生命的张力、生活的打磨因此也就在这特有的热气腾腾的状态中前行与升华。老街人的高兴与哀愁,幸运与不幸就在这热气腾腾的编码中浮出水面、浮上心头,像极了张择端的那幅《清明上河图》:烟铺、鱼市、澡堂、杂货店……琳琅满目,程旭升、葛大宝、赵小发、江八奶奶……熙熙攘攘,每一处都是吴春富从老街的石阶上、过往中拾起来的草木与尘埃,既沁人心脾也呛人肺腑,每一缕都是老街上空的阳光、月光与星光,既是卑微的,也是日常的,既在叩门,也在叩问,明喻、隐喻、暗喻地分解着老街人生活的枝枝叶叶、坎坎坷坷,分享着、拓展着这个作为诗意的热气腾腾的本质。

他将大号锅烧红,然后抡起大铁瓢舀了些猪油,沿锅沿一转,划了道闪亮的弧线……
一道闪亮的弧线,划过老街的麻石条,也划过你我读者的心灵深处,以及沉淀在读者心灵深处的搪瓷缸、八仙桌、被黄烟熏得通黄的老街一行人的手指。还有比这更香馨、更具有烟火味的弧线吗!尽管这香馨是呛人的,这烟火味也是呛人的。
店主刘三爷搬了张凳子靠桌边坐着,眼睛睃着街面,他右手常年吊着个黄烟袋……
我喜欢这个“睃”字,它让有些沉闷、凝滞的老街一下子灵动了起来,就连那市侩味也充满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性。在它的背后,我几乎能读出文本发生学的解码,即文本发生前的老街:烧饼、油条、包子、米饺……样样不缺样样缺,样样钻营投机样样体现出爱与友善。
薛爱英出门估摸半个时辰,葛皮起床了。漂漂在锅灶底下的柴火堆里卧着,听见响声,立即起来抖抖皮毛。葛皮也不刷牙,揩了把脸,把黄杆子票往褂子腰里一揣,拿了一个浅绿色的瓷碗就要出门……
不可否认,生活就是这个样子,老街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可以不刷牙,狗在柴火堆时卧着,东西往褂子腰里一揣。
摆了两张桃木打的八仙桌子,黄爽爽的,散发着桐油的清香……
活生生的生活就在这“散发着桐油的清香”的潜移默化中生成并行走,月光下、阳光中、店铺里。
我无意为吴春富的这部小说贴上诗意的标签。这或许真就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老街的明月与其他地方的明月是一样的阴,一样的晴,一样的圆,一样的缺,一样的亘古不变又亘古有别。但《老街》的月亮又是吴春富画出的那一轮,它无可争议地属于吴春富独有。所以,吴春富画出的《老街》中的每一页照见的都是吴春富一锹一锹挖出来的“沟渠”,这“沟渠”里有详实而斑驳的人生百态:凶神恶煞的王桂华,钻营投机的高新潮,助人为乐的程旭升,等等,他们既灰不溜湫,又荣光焕发,素描、白描铺就的爱恨情仇,既蜻蜓点水,又大张旗鼓。
……然后弓起手指轻轻刮着赵昆仑的小嘴。赵昆仑笑得更欢。倪菊花更开心,她摸着自己滚圆的肚子说:小兰,我这肚子里也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

知与不知并不重要,男孩还是女孩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超出文本之外的链结性。《老街》虽洋洋洒洒,但它仍然不能直接把所有需要表达的信息,也就是把“男孩或女孩”用笔墨直接“传递”给我们──那样恰恰相反,《老街》将无法呈现老街。试想,一个堆积如山的“老街”,读者除了窒息,别无选择──我们必须通过文本这个有效的链结性来实现“弓起手指轻轻刮着赵昆仑的小嘴”之外的拓展。这是吴春富们的聪明之举,也是吴春富对那个诗意本质的领悟,他让我们心领神会地通过他提供给我们的选择性记忆,亦即链结性来吹糠见米般拓展出他的这个热气腾腾的《老街》。
链结性是一座桥梁,吴春富无疑建成了这座桥梁,它直抵那个生活的本质,那个存在着的诗意。
常常在网上、纸上及诸多媒体上看到“烟火气”一词。现代社会的快进、快餐、快递让“烟火气”离我们越来越远,这是环保的需要?但从文化的角度,这是“环保”了还是“生态”破坏了呢?
“烟火气”是呛人的,但“烟火气”本质上与文化是结缘的,文化与诗意本质上也是结缘的,它们之间同样无可争议地具有链结性,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是一致的──我又一次提到了“本质”──我认为,就是这个一致性让吴春富及其《老街》自觉不自觉地通过了这座他自己建造的桥梁,找到了那个沉淀在年代深处且几乎没有被玷污的有些原始意味的让现代人重新致敬的生活及其方式。这里所提玷污所提原始皆指相对于工业文明及其附属品而言,而非其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致敬不等于重温。那样的生活无论如何是不可重温的,它仅仅只能属于远方的灯火,但灯火栏栅。
一切生命都来自于大地,即便是广阔无边的海洋也仍然是大地的一部分。老街也是如此:那些铁匠铺、篾匠铺、雕匠铺、钟表铺,那些鱼行、茶馆、大锅台,那些脸色苦啾啾的,那些心情急抓抓的,那些眼睛睃一下,那些潮气炕灶里炕一下,那些炆蛋、炸春卷、冻米糖……每一星都在大地之上,大地具有无穷的引力,这个无穷的引力让处在大地上的一切永远蓬蓬勃勃,我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蹙因之诗意盎然,美不胜收。
普鲁斯特曾在他的《追忆似水年华》中说过:“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我的观点一直与此不怎么等同。我总是主张,既然仍然感觉到它是幸福的,那它便没有失去,它仍然在我们手中。
老街上的一切均在吴春富的手中,我因此感觉到,吴春富对老街的感觉是幸福的,甚至始终幸福。幸福与苦痛一样本质上都是诗意的。
当然,吴春富将老街既蜻蜓点水又大张旗鼓地兑换成了《老街》。如此而已。
本文作者简介: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屠家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庆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天津文学》《散文》《散文海外版》《清明》《山东文学》《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当代人》《青海湖》《安徽文学》《奔流》《散文百家》《散文选刊》等50余家省以上报刊。作品多次在国家及省内外获奖。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散文集《大地苍茫》及绘本《黄梢子,出发!》等。
中国新闻社安徽分社版权所有:刊用本网站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主办单位:中国新闻社安徽分社 地址:安徽合肥梅山路8号 邮编:230021
联系电话:0551-65533351 投稿信箱:anhui@chinanews.com.cn